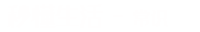我毕业后 , 她也改行步入政界 。 我始终对她敬重有加 , 她对我的关爱也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减弱 。 我毫不怀疑 , 她是接受了天使的派遣 , 成了我近乎姐姐一样的亲人 。
乡村教堂坐落在土路边 , 再往前五华里就到了小镇罗桥 。 站在二楼的教室远眺教堂 , 是沙砾一般大的黄点 。 星期天 , 我爱去那儿 。 教堂是一栋二层洋房 , 泥黄色 , 房顶呈三角形 , 避雷针一样的塔尖把它从凡尘中剥离出来——尖细的 , 形而上的 , 仰望的 。
它还是孤单的 。 四周是矮小的山包 , 不远处有一个荒废的打靶场 , 杉树林被压在低坳 , 只有树梢摇摆在视野里 , 土路也偶尔晃过一个骑自行车的小贩 。 信徒并不多 , 他(她)们从远近的乡镇跑来 , 背一个布袋 。 布袋里是《新旧约》 , 几块零票 , 记录赞美诗的小学生作业本 。 他(她)们的神情庄严 , 静默 , 有一种慈仁(也像茫然的麻木) 。 大厅稀疏地容纳了十几人 , 兄弟姐妹们相互交谈 , 问好 , 祝福 。 时光在祈祷 , 弥撒 , 圣乐中镀上了仁爱的光泽 。
很难说清他(她)们的神色和内心 , 是什么样的 。 脸上还有路途的灰尘和疲倦 , 脚上是黄土 , 低垂的眼神散发光一样的圣洁 。 他(她)们的苦埋在黑暗的(内心的)土层里 , 只在袒露的肌肤上刻划苍老的纹路 , 而赞美诗仿佛河水 , 洗去悲与愁 。 圣乐分清唱剧、弥撒曲、安魂曲 。 我最爱弥撒曲 , 尤其是大弥撒中的《圣哉经》:
圣哉 , 圣哉 , 圣哉!
上帝 ,
全权又全能的主 。
天和地
都充盈着
你崇高的形象 。
天上的和撒那 。
弥漫人类虔诚的爱思的《圣哉经》 , 是最古老最庄严的合唱 。 它与《慈悲经》、《荣耀经》、《信经》、《羔羊经》 , 组成了大弥撒 。 安魂曲虽然充满亡灵的哀伤 , 但显得华丽 。
我坐在他(她)们的中间(却不是其中之一 。 唱完安魂曲 , 我也应和一句“主啊 , 拯救我” ) , 也能接受圣洁的洗礼 。 那时我对神父有心往神驰的迷恋 , 宽大黑色的长袍暗藏了一个神秘的世界 。 但我至今未看过神父——我生命的某种神性的缺席 。 2000年秋 , 我对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人说 , 我的婚礼要放在教堂举行 , 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
前几天 , 我读周晓枫的《圣诞节的零点》 , 莫名的激动和伤感涌上心头 , 青春的时光竟然模糊地翻滚而来 , 像一张没洗好的黑白照 。 我操起电话就打给县城的同学徐勇 。 我说 , 教堂还在吗?他还以为我要买那栋房子 , 说 , 被一家私人诊所占了 , 在打官司 。 我说我只想看看 。 我妻子蔡虹说 , 三江那边有一个 。 “我在上海读书时 , 我孃孃经常带我去教堂 。 那儿真是华美 。 ”她又说 。 我说 , 上帝是一样的 , 但教堂不一样 。 但我最终没去寻找 。 那片原野 , 已经永远消失在繁华的滚滚红尘中 , 在这十年中 , 高楼和广场像鳄鱼一样把它吞噬 , 高速路、外环路如同两块刀片留下的伤疤 。 说实在的 , 我也找不到教堂了 , 连大概的方位都摸不准 。 找到了又怎么样?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丝绸之路|体验杏花之美,一定要上帕米尔高原!
- 高原|26张极致大片,寻找地球最美的角落
- 防风|十一旅游高原必备衣物篇 千万不要追悔莫及
- 融创雪|冬奥特稿|云南冰雪运动实现从无到有 助推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
- 地方|又到自驾西藏季节:看看我总结的高原行小常识,总有一条对你有用
- 攻略|帕米尔高原在什么地方,春天南疆帕米尔高原杏花村5天6夜自由行赏花攻略
- 高原|贴心!移民签证过期不需要重签啦!
- 高原|给我六天时间,进入“香巴拉”
- 帕米尔|新疆帕米尔高原新晋网红公路,全程639个弯道!你敢来此开车吗?
- 高原|青藏高原和玻利维亚高原的海拔高度差不多,为什么难形成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