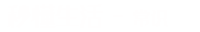语文在师范的课程里一分为二 , 分为语基和文选 。 我从小就不怎么喜欢语文 , 死记硬背 , 偷不了懒 , 不如数理化变化大 。 皮晓瑶老师教我文选 。 她剪一头指长的短发 , 上课的时候 , 脸上飞翔霞一样的绯色 , 她的嗓音低沉圆润 , 有穿透力 , 音质甘甜 。 我非常喜欢她的课——不是爱语文 , 而是爱听她的声音 。 我甚至有点畏惧她 , 倒不是说她严厉 , 也不是我露怯 , 而是我由衷敬慕她 。 事实上 , 她是一个和蔼的人 , 虽然只长我5岁 , 与班上年龄最大的祝洪春同年 。 她的温爱与教养是其他老师所不能比的 。 她的气质像暗夜的光晕 , 笼罩我们 。
她是与众不同的 , 至少我这样认为 。 她不会让我们记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之类的死东西 , 也不会要我们背课文 。 她注重时代背景的诠释 , 向我们铺叙作家一生的历程 。 她广博的文学知识和素养 , 与她的年龄是不相称的 。 于我而言 , 她打开的不是一扇窗口 , 而是广袤的旷野 。 我看到金黄的秋色 , 蔚蓝的加勒比海的波涛 , 俄冈山的白雪 。 她向我们介绍的作家 , 我几乎阅读了他(她)们的所有代表作 。 她一边讲解一边谈自己的读书心得——她是动情的 , 抑扬顿挫的声调夹缠了她往昔曼丽的时光 。 只有阅读课文的时候 , 她起个头 , 叫学生接力下去 。 通常第一个被点名的是乐建华 。 他的父母是上海知青 , 在县城工作 , 多年后 , 他父母和弟弟去了上海 , 他成了故乡里的异乡人 。 我们都以为他会去上海 , 想不到他几经辗转 , 前两年到农村当了武装部长 。 去年我和同学徐永俊到乡下探望他 , 他坐在农家的八仙桌上吃饭 , 穿一双解放鞋 , 聊农事 , 我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 。 我说:“生活委屈你了 。 但我为你感到高兴” 。 他的由高到低的生活 , 剥夺了年轻人的浮躁气 。 生活是泥沙俱下的 , 磅礴的力量会形成巨大的黑洞 , 人是被吸附的尘埃 。 那时 , 他是全校最时尚的人 , 象棋纵横全区校园 , 他的温文尔雅在女生中有广阔的“市场” 。 他朗读极有节奏感 , 有磁性 。 一般的情况下我是接他的 。 我普通话有方言的杂音 , 又没有情感的起伏 , 糟糕透了 。 皮老师选我 , 完全是出于偏爱——我全力以赴投入文学的样子 , 即使在全校也是凤毛麟角的 。
我疯狂地爱俄罗斯文学和英国文学 , 坚韧的饱含苦难的阿赫马托娃 , 尖利的维茨塔涅娃 , 被情欲焚烧的普希金 , 早夭的拜伦和齐慈 , 仿佛苍穹上璀璨的星辰 , 给我心灵抚慰 。 我没有吸收到俄罗斯的像火一样的血液 , 却怀有它黑夜无垠的忧郁 。 《日瓦戈医生》、《猎人笔记》成为我的至爱 。 但我讨厌契可夫 , 烦透了高尔基 。 没有图书馆 , 我四处举借 。 我晚自习的时间 , 几乎是花在抄写外国诗人诗选上 , 乐此不疲 。 《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一直是我渴望阅读的书 , 我借处无门 , 就向皮老师开口 。 这种书 , 一般人是不轻易外借的 , 没想到她满口答应 。 在她家 , 我很不安地左手玩右手 , 跟在她身后 , 爬上阁楼 。 阁楼有些暗 , 许多包扎好的纸箱 , 码成排 。 她很快从其中之一的纸箱中 , 找出托尔斯泰的惊世之作 。 “你要保管好 , 不要弄脏了 。 ”她说 , “我在大学的时候 , 就非常爱读托翁的书” 。 我打开书 , 看见扉页上有她先生的签名和赠言 。 这是她爱情的信物 , 也是她青春的见证 。 我一时无语 , 眼眶湿湿的 。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丝绸之路|体验杏花之美,一定要上帕米尔高原!
- 高原|26张极致大片,寻找地球最美的角落
- 防风|十一旅游高原必备衣物篇 千万不要追悔莫及
- 融创雪|冬奥特稿|云南冰雪运动实现从无到有 助推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
- 地方|又到自驾西藏季节:看看我总结的高原行小常识,总有一条对你有用
- 攻略|帕米尔高原在什么地方,春天南疆帕米尔高原杏花村5天6夜自由行赏花攻略
- 高原|贴心!移民签证过期不需要重签啦!
- 高原|给我六天时间,进入“香巴拉”
- 帕米尔|新疆帕米尔高原新晋网红公路,全程639个弯道!你敢来此开车吗?
- 高原|青藏高原和玻利维亚高原的海拔高度差不多,为什么难形成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