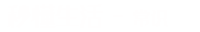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春天的时候,那时我们家吃菜的次数会多上一些,因为树上和田野里都会长出丰富的食材了,槐花、榆钱、灰灰菜……母亲常常会采来这些新鲜的菜,给我们蒸着吃 。我记得在很多个清冷的早晨,我下了自习回家,远远看到我家烟囱上徐徐飘散的白色炊烟,便会心生欢喜 。这样的炊烟表示这天的早饭肯定不止是白汤白馒头了 。果然,一进院子我就闻到蒸菜的清香了 。在厨房的腾腾烟雾里,我看到母亲把地锅中一满篦子的蒸槐花或其他菜起出来倒进大陶盆里,然后拌上早已调好味儿的醋汁儿蒜泥进行搅拌 。不一会儿,一盆鲜香的蒸菜便调好了,母亲会给我和弟弟各盛上一满碗,然后我们三口坐在氤氲着春天清香气息的小院子里,吃得无比开心 。
可春天匆匆离去后,有菜吃的日子就会又消失了 。不过,熬到蝉鸣蛙噪的时候,我们的伙食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时母亲会用“爬蚱”和苋菜咸汤来调剂每天清淡的三餐 。“爬蚱”就是知了褪壳前的样子,每天日落后它们便会从地底拱出地面,爬到树上准备“变身”,这时的肉质最鲜嫩了 。所以村里的老老少少一吃过晚饭便会打着手电筒、扛着长竹竿、提着一个大大的塑料桶去巡视村内外的每一棵大小树,也就是“摸爬蚱” 。有的人一晚上能摸上百只呢 。
摸回的“爬蚱”先要用盐水泡上一晚吐污,待吃的时候不管是煎是炸是炒是炕,都是一道香味扑鼻的小荤菜 。母亲最爱把爬蚱给我们炕了吃:锅里倒上一点儿油后,把洗干净的爬蚱倒进去,然后用铲子压着勺子在烧热的干锅里炕爬蚱,最后再撒上些盐巴……吃起来时那叫一口一个香 。
当然我最爱的还是炎炎夏日里的那碗苋菜咸汤,我们那儿又把苋菜叫成“玉果菜” 。夏日蓬勃的生机为田野和树林里带去了无数的玉果菜,而且不管人们怎么掐干净它的嫩叶,它都还能重新长出来,也就是所谓的取之不竭吧 。我还记得在一个又一个喧嚣又酷热的正午,望着我们饥饿又期待的眼神,愁容满面的母亲便会出门去树林、田间地头转上好久,然后带回来一大把新掐来的玉果菜头准备烧咸汤 。
一般她都会先找来一个番茄切块儿烹炒,然后往锅里兑入几碗水,待锅滚水开后再倒入先前搅好的一碗面糊,等二次滚锅后便将洗净的玉果菜叶按进锅里,三次滚锅时再将一个鸡蛋打个小孔、把蛋液一缕一缕地“甩”进锅里,然后撒上盐巴、十三香等调料,这样一锅香喷喷的玉果菜咸汤便算完成了 。自然生长的番茄为菜汤添入了点点的酸味儿,野生的玉果菜则是清新爽口,鲜美微酸的咸汤我一个人就能喝上三碗呢 。这个时候我会暂时忘记生活的艰难与苦涩,因为玉果菜咸汤的美味足以让我感受到世界的灿烂美好 。
秋天的时候,锅里依然不见菜 。家里的气氛也随着温度降了下去,母亲找不来菜给我们吃了,她偶尔便会去镇上批发一些便宜的辣条回来,让我和弟弟就着馍吃 。热腾腾的馒头夹着辣条,总比干馍或者“油馍盐”好吃太多吧 。
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依然极少吃炒菜 。也许是因为省着买菜、用油的钱,也许是因为家里就一口地锅,用的还是得费力提回来的井水,倒腾炒菜和烧汤很不方便,反正厨房里最多出现的还是凉拌萝卜丝儿 。乡下冬天的白萝卜太便宜,母亲总是把买来的萝卜切成一条条白嫩的细丝儿,然后在碗里用盐、香油和醋拌好,给我们当下馍菜 。热馍就着酸、咸的萝卜丝儿,也很爽口呢 。当时正在长身体的我,只要这一点儿菜也能咽下去两三个大馍呢 。
当然,天寒地冻的时候,母亲偶尔还会给我们熬上一锅“辣椒糊糊”:干辣椒剁碎爆炒后倒上水,放入一小把虾皮,然后搅上稠稠的面糊熬成一锅糊涂,滚锅的时候再打入个鸡蛋,在锅里搅得稀碎,最后拌上调味料……在寒冷的冬天,那一勺勺被飞快送进嘴里的辣椒糊糊,其香辣鲜的味道帮我们驱走了漫长的严寒 。
除了冰凉的凉拌萝卜丝儿和偶尔才吃的辣椒糊糊,乏味儿的冬季里,母亲还会给急需营养的孩子们做“鸡蛋蒜”吃 。乡下冬天的大蒜也很便宜,母亲总会先让我们帮她剥上一大把蒜瓣儿,然后把这些白胖的蒜瓣儿在蒜臼里捣碎,倒上些水、醋和盐拌匀,然后将一个煮好的鸡蛋剥了皮儿按进蒜臼里捣碎,和蒜泥儿一起拌均匀后再滴上两滴香油……于是一份不乏营养又咸、辣可口的“鸡蛋蒜”便大功告成了 。我最喜欢掰开馍夹着一层鸡蛋蒜吃,不过吃到最后往往会被蒜辣得猛喝汤 。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西班牙流浪汉小说 流浪汉小说
- 小米辣与树椒的区别
- 啤酒烤鸭的制作以及配料
- 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
- 替代通知金的标准是什么
- 乃夜发书发的意思
- 烤漆门的材质是什么呢
- 在兴隆,寻一间咖啡馆
- airpods双击哪里
- 刚买的手机有别人人的照片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