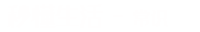秉笔史氏成功与否 , 后人评说不一 , 但作品本身已成坊间传奇 。 美国顶级知识分子期刊《纽约书评》对史景迁的介绍是“他是《王氏之死》……等书的作者” 。
掩卷之时 , 我惊讶于故事结束得如此突然 。 史景迁本人对自己讲的故事是否满意呢?我后悔见面时没问 , 即便当时我想到问 , 也会难于启齿吧 。 斯人已逝 , 但他早已把回答写在了自己的书里 , 留给有心人去寻找 。 在撰写这篇回忆时 , 我意外地在他的早期文集中读到他对自己工作的思考:
我们所有人在不久之后也会被取代 ,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取代 。 长年的研究和写作将被证明是易变的或不充分的 。 新的文本会出现 , 或者旧的文本会被重估;新的主题会吸引学者及其读者;对过去的新方法会把旧的推到一边 。 ……学术研究本身充满了一种勉强可控的疯狂 。 我们在力所能及时勉力而为 , 准备着吃苦或得到回报——也许两者兼有 。 如果我们选择对我们全部的研究什么都不做 , 不写下来 , 不权衡 , 不公开我们的想法 , 那么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保护 , 但这是一种怯懦的保护 , 一种躲避追求真正知识的保护 。 在我们的缄默中 , 我们仍然可以成为审视者 , 甚至可以平静地注视着全局 , 但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参与到学术争辩的最深处 。 (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1993, pp.5-7.中译本名为《中国纵横》 , 以下引文同此出处)
原来“像天使一样写作”(列文森语)的史景迁也有过彷徨的时刻 。 他经常自况的人物 , 并不是什么伟人或大师 , 而是历史上为某一写作执念而痴迷的人 , 比如欧洲第一本介绍中国语言著作的作者巴耶尔(Theophilius Siegfried Bayer , 1694-1738) 。 史景迁如此转述研究汉语的执念突然降临到巴耶尔身上的时刻:
突然间学习中文的渴望排山倒海地将我淹没 。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 我努力工作 , 思考——或者说是做梦——如何深入了解这门神秘的学科 。 只要我能在这一领域产生一些小东西 , 我便会认为自己是神的孙子和王中之王 。 我就像一只怀孕的兔子 , 在我的洞穴里收集一切东西 , 我可以找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编成某种字典和一些关于中国语言规则和中国文学的介绍 。
2018年 , 史景迁在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的获奖感言中写道:“我在很久以前便与中国及其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 我在上了几堂现代汉语课之后 , 便深感中国历史、艺术史和文学的浩瀚无垠 , 可供我上下求索 。 于是 , 在六十多年前 , 我开始对中国着迷 , 从此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去追求别的事业 。 ”我想 , 他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自己掉入“兔子洞”的故事 。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鲜活的版本: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环球|年味满满!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开启首个“环球中国年”
- 中国|洪洞大槐树景区:第十六届民俗中国年暨夜游活动超前剧透
- 桑拿|2021年中国桑拿城市,重庆意外落榜,广州武汉桂林海口等纷纷上榜
- 长沙|新加坡用奶茶“对话”中国消费者 推销“狮城”旅游
-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慢火车”旅行:放慢脚步 感受“诗和远方”
-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以无障碍传递无障“爱” 延庆冬残奥颁奖广场具备赛时运行条件
- 恒大冰泉|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考察组到长白山老黑河遗址参观考察
- 吉林|吉林陨石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陨石为主题的博物馆
- 大连|中国八大宜居城市新排名,倘若择一城终老,这八座城你会选哪个?
- 房车|他花30万改造房车,带娃自驾环游中国,太令人羡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