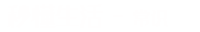文章插图
王昭君像
直到时代更晚的刘辰翁评点王安石诗时,才对《明妃曲》稍稍恢复了“文学”的解读 。他解释“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这几句,是昭君家人宽慰远在塞外的昭君之语,是王安石代拟其家人寄言而非诗人本人所发之议论;这样,“人生失意无南北”读起来就“但见蔼然”而“无嫌南北”了,因为诗中表达的是感人至深的亲亲之爱,这种普泛之爱是超越地域和民族的,是不分南北或夷夏的,是人情之常 。至于“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刘辰翁解释说这是正话反说,就像《诗经·小雅》中的《小弁》一诗,“怨”的本质实际是“亲亲”之“仁”;所以这两句诗道尽了被君王疏远的孤臣的哀怨,读之可以令人断肠;认为这两句诗是“无君无父”之意的,实是不懂诗人之“怨”正是“忠”的体现 。刘辰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不受那些利用历史是非将王安石“小人化”的议论的影响,而以一种较为纯粹的文学批评态度来看待王安石的《明妃曲》,对此诗作出了比较公允的阐释和评价 。
从宋人尤其是南宋人对王安石《明妃曲》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一种“诗如其人”的评价倾向 。在宋人看来,“诗”就是诗人的“心中事”,换句话说,诗歌表达了诗人的志意、反映了诗人的心术 。受此文学观念影响,宋代诗人固然更加注重个人修养与道德追求,但在批评鉴赏领域,它也容易带来重教化而轻审美、穿凿附会等迂腐之论的出现,结果就会出现将诗品与人品牢固地捆绑在一起,由此达到褒扬或批判目的的情况 。宋人通过批判王安石之“奸”而揭露《明妃曲》的“心怀异志”,又通过批评《明妃曲》的“险恶”进一步坐实王安石心术的“奸邪”,由此形成了一个看似合理实则荒谬的阐释怪圈 。尤其是,当这种阐释方式脱离了文学批评的范畴,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理性探究,而羼杂了党争倾轧、政治清算等复杂因素时,其带来的恶劣后果,就不仅仅是对文学审美的破坏,更还容易沦为党争、政争时打压对手、杀人诛心的手段和工具 。宋代出现的大量“文字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像范冲、宋高宗之流想要极力证明王安石的“奸邪”,但他们还没有丧心病狂到将王安石的大多数诗歌都锻炼成狱的地步 。实际上,并非没有人这么想过,据《龟山语录》记载,杨时的某位弟子就曾说:可以从王安石晚年诗中作“讥诮神宗”的注脚而定其“谤讪宗庙”之罪 。杨时是程颐的弟子,程门与荆公新学有学术大道之争,杨时本人就曾向宋钦宗痛斥王安石“心术不正”“邪说害人”,但他对弟子提出的这种通过“文字狱”打击对手的方式却极力反对并加以申斥 。正如杨时所说:君子做事,当遵循道理,不能因为当今人人都去揭发别人的诗文谤讪朝政,我们也便去学他;况且以“谤讪”罪名禁止人规谏朝政、言论得失,乃是“无道”的表现,更加不能效尤 。可见杨时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一旦以深文周纳的方式牵扯出浩大无休止的文字狱,并由此形成一种政治上的惯例的话,造成的灾难将不仅是某个个人的,而是整个文人士大夫集团的 。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心态,所以整个南宋时期将王安石贬斥为“小人”或“奸臣”的议论声虽不绝于耳,但像范冲评《明妃曲》那样以“大义”名分攻击他人心术的论诗方式(类似情况或许还有《商鞅》一诗),却较少发生在宋人对王安石其他诗歌的评价上 。恰恰相反,当宋人摆脱了党争、政治等其他因素的干扰,而以较为纯粹的文学眼光看待王安石及其诗歌时,就呈现出了一派完全不同的光景了 。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王安石 书湖阴先生壁
- 中华文明五千年,为何易中天却坚称只有3700年文明,否定5000年?
- 桂林十大最美景点:黄布倒影上榜,第八是千年梯田
- 王安石称呼王临川的由来
- 铁树开了花下一句
- 王安石代表作品
- 曼珠沙华的经典语录
- 求HP同人小说男主萨拉查
- 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句被误解了上千年的诗!
- 西津渡|徒步西津渡 一眼望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