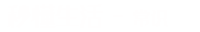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贾志红:沿着尼日尔河行走( 二 )
一个巨大的“几”字 , 就这样画在西部非洲辽阔的原野上 。 和众多的陌生的河流一样 , 在没有真实地走进它的波光里之前 , 我不懂得它的心声 。
所以 , 我也不懂得凝望它 。
【|贾志红:沿着尼日尔河行走】一条河流 , 一条异域的河流 , 它会那么容易地让我懂得它的心声吗?
我不知道 , 我只是在行走 , 在它的波光粼粼里行走 , 在它的浊浪滚滚里行走 。 很多时候 , 这种行走没有任何目的 , 也没有任何思索 , 只是习惯地行走 。
比如在那个暴雨骤停的雨季的午后 , 我走在巴马科最繁华的临河大道上 , 越过拥挤嘈杂的车流 , 我看见尼日尔河浊浪滚滚 , 两岸的树木都淹没在上涨的河水中 。 这个号称“鳄鱼之都”的城市 , 因为这条宽广的河流而平添了几分大气 。
或许这个作为一国之都的城市太喧嚣 , 这不是我喜欢久留的地方 , 也不是我想静谧地凝望一条河流的地方 。
那么 , 我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凝望它的呢?是在塞古吗?这座古老的城市 , 曾经是班巴拉帝国的首都 , 现在它仍是马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 塞古的尼日尔河畔 , 在傍晚时总是聚集了太多洗衣取水的人们 , 他们在夕阳下 , 是劳作也是嬉戏 。 妇女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裸了身体 , 旁若无人地清洗自己 。 她们洗澡的动作宛如原始的舞蹈 。 一块艳丽的花布 , 随意地往身上一裹 , 袅袅娜娜地走来时 , 又是别具风情的一幅画 。 我不知道在两百多年前 , 西方殖民者从西海岸出发 , 沿着尼日尔河探险 , 到达这个尼日尔河上游最古老的城市时 , 是否也惊奇地看到了这一幅原始拙美的画 。 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个西方人蒙哥帕克在日记里赞叹“尼日尔河在阳光中闪烁着波光 , 河上无数独木舟穿梭 , 如泰晤士河流过威斯敏斯特一样 , 庄严地缓缓往东流去”时 , 是以一个殖民者的身份在狠狠地窃喜呢 , 还是如我般只是用纯粹的欣赏的眼光为这幅图淡淡地镶上一个单纯的画框?
这些 , 我不得而知 。 但我知道 , 从此以后的一百多年里 , 这条河流不再庄严 , 或者说 , 缓缓东流的尼日尔河 , 见证了太多太多不再庄严的事情 。
塞古的尼日尔河畔 , 至今还完好地保留着一八九二年征服塞古的法国军人路易阿奇纳将军的塑像 。 他耸立在高高的台子上 , 却背对着尼日尔河而立 。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寓意的象征 , 或许就像殖民时期的黑人妇女们见到法国官员时 , 都要以背相对 , 以示敬意?这位不可一世的征服者沿着尼日尔河征战多年 , 最终是不是也对这条河流充满了敬意?更确切地说是敬畏?还是有另一个缘由?让他无法面对穿梭在尼日尔河上的舟子?无法正视每一个黄昏沉沉地坠入河里的落日?那轮落日坠落的方向正是他沿河顺流而来的方向 。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四川省|鼓浪屿很美丽,沿着海岸走避开中间的商业街,其实还是很安静的
- 芍药花|沿着国道看南充 一路风光一路景
- 向西|沿着杜埃罗河一路向西
- 大别山|【沿着足迹看变化】安徽霍山:昔日贫困村,今朝变“网红”
- 云中|沿着诗词的足迹,走进“人间仙境”——天山天池!
- 遗址|沿着百年“京门铁路”,了解中国的铁路历史文化
- 丽江|从丽江出发,沿着高速去旅行!前方高能美景奔你而来
- 门头沟|沿着滇越铁路,重温米轨时光!
- 大海|海爷的海
- |景致记录:沿着乡村公路去赏花,樱桃花、阿拉伯婆婆纳、那株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