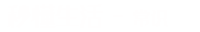崇礼野花甚多,哪一种最能代表崇礼?
那我认为,非毛茛科非常美丽的冀北翠雀花莫属。2016年8月,因我所著的《崇礼野花》快要下厂印制,再次来到崇礼,核实人工改造过的山坡在大雨过后的表现,顺便到崇礼狮子沟乡的一个山沟看看。在山沟里,我见到毛茛科翠雀属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种类,其学名的“种加词”用的是“西湾子”,指的就是崇礼的主城区西湾子。而这种花,正是冀北翠雀花。冀北翠雀花的特点是茎粗壮、上部多分支,花瓣狭长并前伸。其模式标本1862年9月采集于崇礼,采集人是大名鼎鼎的谭卫道。珙桐、麋鹿、大熊猫都与他有关。
崇礼干旱的山坡上,另一种非常特别但完全不引人注意的菊科植物——山蒿。此植物在当地生态系统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冀北翠雀花数量极少,而山蒿满山头都是。能欣赏山蒿的人不多,这需要历史、植物、生态认知的勾连。
蔷薇科榆叶梅在华北地区不算什么稀罕植物,到处都有栽培,野生的也见过许多。尽管它不丑,看多了也不会在意。但在崇礼的“人头山”上,沿废弃的长城生长的大片榆叶梅还是震撼了我,它是那样柔美,与山峦配合得恰到好处。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普通的榆叶梅可以如此神圣,我决定把此线路推荐给朋友,让他们在恰当的时候专程来欣赏榆叶梅。一种植物美不美,没有绝对的标准,要看它与环境与欣赏者具体条件的关系。
说说“哲学”与“博物”
最近十多年,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是试图复兴博物学文化。简单说是从博物的视角重新看待一切,比如重写历史、重新评判文明演化,鼓励人们通过“博物+”将博物要素融入自己的生活和事业。针对的是“现代性”顽疾、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难题。我深知任务艰巨,不是发几篇文章能解决的。
而书写崇礼,是我倡导的博物学行动的一部分,一个小小的实例,跟之前写《勐海植物记》《青山草木》意思一样。虽然个人水平有限,仅对植物稍有点经验,但必须做出若干例子,竖一些靶子,人们才好理解复兴博物学想干什么、如何操作。
除了实践探索之外,我也在思考一些理论问题。比如博物学与科学的关系怎样?哲学工作者为何关注如此感性的博物过程?
之前我列举哲学家中有一批人关心过博物学,比如老子、庄子、朱熹、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F.培根、J.洛克、卢梭、康德、歌德、利奥波德、罗蒂等。但总是觉得勉强。因为通常人们认为哲学是抽象的学问,哲学是形而上的东西,而其他学科或事物是形而下的。
但是,最近我对哲学有一个新看法,反对形而上形而下的划分。笼统讲,哲学是“爱智慧”。首先要注意“爱智慧”不等于“智慧”本身,哲学强调的是一个过程,一个动宾结构。其次,这种爱智慧的动作并非只发生于对概念的抽象思考之中,而是贯穿于人类活动的各个层次。哲学家那里有哲学,科学家那里有,商人、工匠、农夫那里也有,只不过他们没有用学院式的语言表述出来罢了。此外,既然所有学科的划分都是相对的、人为的,而世界及遇到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体,那么,就需要打破学科的人为划分,用综合的手法解决。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元宝|山西平遥:千年古城春意浓
- 古城|山西平遥:千年古城春意浓
- 山西|山西平遥:千年古城春意浓
- 平遥|山西平遥:千年古城春意浓
- 光明日报|在崇礼,有一座“绿色”冰雪小镇
- 西藏旅游|净月潭里的金代墓地,为何有石羊石虎?原始崇拜让人敬畏!
- 金代|跨越800年的绽放——崇礼太子城演变记
- 秘境|江西靖安:白云深处的山水秘境
- 上海市|山西有个“大寺”,始建于金代,占地4000平方米,古朴又壮观
- 暴风眼|在暴风眼中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