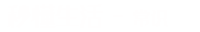文/陈波
高峡、平湖,秋水、长天,潋滟、空濛……驻足湖边,脑子里像泄洪一样,淌出这一长串的词语。尽管这峡不是三峡,这水不是赣江,这湖也不是西湖。
湖的前半生,是一条河。河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消极的河抑制不了汛期的躁动,暴饮暴食、寻衅滋事,留下一个个关于河妖的传说。河是丰满的,又是骨感的,骨感的河在层山叠嶂间勾勒出美丽的曲线,青黄不接的乳汁难以背负起母亲河的盛名。为改变河的消极、填补河的骨感,便有了湖的构想,然后修建、储蓄、成型,再至利用、维护、开发。
【 钟湖|行游|陈波:行走升钟湖】在原本纤瘦的西河上,拦腰筑一道坝,锁住河的七寸,蓄起一片13亿立方米的水域,这片水域便是现在横亘在眼前的湖。湖就地取名,叫升钟湖,洋溢着阳刚之气,赓续着升保起义的红色血脉。湖又名西水湖,与西湖相比,倒真是多了不少的水,但西湖的名声实在太大,拒绝吃软饭的南部人便把西水湖这个充满风情的名字束之高阁了。
潭面无风镜未磨——湖的最大特点是静,观湖却需要动起来。观湖的路线有两条。
一条是水路,舟行碧波上,铁皮游船,粗犷的开船汉子,轰鸣的马达声,惊起的水鸟与鲢鱼,一切是那么自然与生动、真实与淳朴。把水踩在脚下,山就成了参照物。高大的峰挺直脊梁,仍以山的姿态俯瞰着湖;低矮的丘在湖水的柔情里沦陷,甘愿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成了只钟情于湖的岛。
另一条是陆路,车行林荫中,沿湖滨路一周,在间种的垂柳、法国梧桐、水杉、黄桷树中穿梭。如果你去过西湖苏堤、南京紫金山、武汉东湖、安顺白水河,那些沉睡的记忆一定会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中苏醒。岸边的山把人吞噬,宽阔的湖面又成了参照物。湖是成了大器的河,湖面平静、湖底汹涌,湖装着山的脸色、天的脸色,却把自己的脸色隐藏了起来。
瞥见一棵参天古樟,不自觉地停了下来。古樟长在停车场的北面,紧挨停车场南面的是水码头。无论走水路还是陆路,只要你想在码头或车场停靠,就一定会看到这棵活成了地标的树。
古樟老当益壮、郁郁葱葱,不知道已完成多少个“十年树木”的阶段性目标,坚定地走着“百年树木”的路。古樟与湖面相互凝视,默契地用精神意念向那些打着“百年树人”口号、抄着“十年树人”近道的短视者发起挑战。
湖当然不是没有度量的。一场罕见的雨让上游的名城阆中再次上了新闻。洪水夹着泥沙劈头盖脸地向湖打来,湖张开怀抱,微笑着接纳洪水。洪水为湖的实力所震慑,为湖的气度所感化,从冲动变为平静,从浑噩变为清澈。
湖是做出了自我牺牲的,湖的生命线——大坝使出洪荒之力,用坚不可摧的牢固诠释着对湖的忠诚;湖的事业线——水域小心翼翼地向两岸扩张,在进取中极力维护着湖的英名;湖的感情线——亲水走廊被升起的水位线淹没一半,湖的众多仰慕者被挡在岸上,留下一段未能成愿的廊桥遗梦。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小小说|行游|郑良:赏雪去
- 王成志|行游|王成志:游逛重庆十八梯
- 成都|丹景台将再添一条上山游道 预计春节后可通行游览
- 台中|成都丹景台将再添一条上山游道 预计春节后可通行游览
- 长福|图片精选 | 且行且摄,跟着美图行游世界
- 雅安|行游|张永春:川西游记
- 智慧文旅|“一键游渝中”平台上线 吃住行游购娱一键搞定
- 新闻|中国交通新闻|“八桂文旅号”开启旅行游玩新模式 广西首辆专属定制高级旅游列车下线交付
- 杂文选刊|行游|廖天元:愿揽冬阳长照君
- 曼谷|去泰国旅游,为何懂行游客都不去曼谷看景点了?有更好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