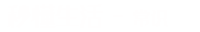新党|秦观的忧伤:可堪孤馆闭春寒( 二 )

文章插图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这八个字犹如温泉,让这首词有了丝丝暖意——还有朋友在惦记他。岁月无情,能温润无情岁月的只有这点点牵挂。秦观无疑是幸运的,至少还能在孤独中读到朋友的来信,而我们却只能对着手机,在陌生人无聊的笑声中沉沦。按我的设想,这八个字理应成为这阙词的转折,由沉闷到欢愉,至少也应增添几分笑意。可惜我错了。这或许就是普罗大众与天才的区别。
朋友的慰藉,堆积在词人的心中,成愁成恨。“砌”,不是砌砖,不是砌墙,而是砌恨。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的“恨”是时间上的,是虚的;秦观的“恨”却是空间上的,是实的。把这些“恨”堆砌在心上,人还能呼吸吗?怕是只能苟延残喘了。中国的文学向来讲究虚实相间,笑着的可能在哭,喧哗的可能很寂寞。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大概如是吧。
更为可笑的是,他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恨谁”。他天资聪颖,博览群书,精研兵法,一心想治学想治国,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他只能躲在一个破旧的旅舍里独自舔舐着自己的伤口。这对一个身怀大志的中年来说,绝对是一种莫大的屈辱。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哪里才是出路?在这种极端苦闷的心境之下,词人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天问”——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人生无论长短,世界无论多大,但在自己身边绕来绕去的诗中还是那么几个人。自己就像一粒丝瓜的种子,即便已经用尽了全部的精血,依然还是在这堵墙上打转。你的悲伤,你的幸福,全系于此。就如同眼前的郴江,它围绕着郴山流淌,自由来源于此,拘束也来源于此,它一生的荣辱都依赖于此,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若说不幸,它至少也是在欢快地流淌。若说是幸,可它为什么不肯停留?为什么不舍昼夜不知疲倦地往前流淌。就像我的泪。
文章插图
欧阳修曾“泪眼问花”,辛弃疾曾问过“郁孤台下清江水”,纳兰容若曾问过自己“一往情深深几许”,但在我看来,都没有秦观的这一问更疼彻心扉!他似乎没有退路了,读过的书,学过的道理,完全没有了用处。对于一个书生来说,这无疑会要了他的命。我能想象,一个憔悴的中年人,站在清寒的旅舍内,对着一江春水,默默流泪的场景。这个世界恍然已经与他无关。事实上,这首词写完不久,秦观就与世长辞。
秦观虽是苏轼的学生,但远不如苏轼旷达。苏轼到了儋州,依旧可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过活,但秦观不行。他的词细腻,心更细腻。他将内心所有的委屈与不甘都付诸于郴江水。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就算如此,朝中的当权者还是没有忘记他。公元1099年,秦观被贬雷州(广东)。公元1100年,哲宗皇帝去世,徽宗皇帝继位,苏轼等人的命运也迎来转机。但是已经太晚了。就在同年,秦观在广西横州去世,年仅五十岁。此时距离这首词的写作时间不过两三年而已。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府城|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润富”之道
- 历史|云南有座没有城墙的古城,与阆中平遥歙县并称保存完好的四大古城
- 涠洲岛|北海涠洲岛三天两夜的旅行实录(含具体出行路线,多图)
- 锅炉|年轻人爱泡的小众私汤,其实都是锅炉烧开水?
- 山西省|山西旅游首选,美不胜收,看看是你的家乡吗?
- 杭州|曾经一房难求、周末爆满的太子酒店,如今住客评价:很安静
- |和一毛不拔的人去旅游,是什么体验?过来人:总算花钱看清人品了
- 空间|深观察|高架下的空间,竟能安放我的乡愁
- 天池|长白山的天池到底有多美?
- 草海|四川广元最热闹的步行街,当地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外地游客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