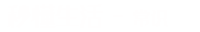娜拉|“娜拉”出走,然后开始漫游︱播客( 五 )
胡卉:我写了几个这样的女性 , 但是她们出走的方式有所不同 。 有一篇叫《逃离》 , 讲一个年轻的女性好不容易在一线城市安下了家 , 却发现丈夫有家暴的倾向 。 她就在犹豫要不要带着年幼的孩子离异 , 因为这个家确实是她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 , 要不要这么快就去做一个把它切割的决定 , 对她来说也很为难 。 还有一篇是讲一个单亲妈妈辞掉了一个小地方医院护士的工作 , 要去薪水更高的深圳打拼 , 还带着自己的儿子跟母亲 。
我看到这个变化的时代里的女性 , 受教育程度更高了 , 行动的自由也更大了 , 但与此同时 , 她们移动的时候背负的东西也更重了 。 我的书写对象们的每次移动 , 每次出走 , 其实她们都是把一些家庭的责任都拿到自己身上来了 。
葛书润:她们不是把家庭抛在后面了 , 反而是会背着这个责任继续出走 。
胡卉:对 , 她出走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 她不是从丈夫的家里走出来 , 把孩子、把婚姻留在那个家里 , 而是带着孩子一起走 。 现在的城市女性都有一定的谋生的能力 , 她们在多年的婚姻生活里习惯了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
葛书润:这可能已经成为了她们的一种惯性 。 你的故事里的这些女性 , 你观察到她们的出走一般是出于什么样的动力呢 , 是对现有生活的不满 , 还是说想去追求个人的价值?
胡卉:可能是就是所有人都会想的 , 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吧 。 但她们都对自身有一份自信 , 才敢去变动 , 才敢挑战新的东西 。
葛书润:你觉得女性在选择从一种生活跳到另一种生活的时候 , 身上的担子会比男性更重一些吗?她们会遇到一些独属于这个性别的阻碍吗?
胡卉:我好像不能够下这个定论 , 因为男人也很难 , 我感觉一个个体加一个个体的社会好像很难去归类 , 只能去看、去分析那个个体 , 她/他是怎么样的、怎么想的 。
葛书润: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困境 , 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的话其实也给我一点启发 , 就是不要把真实的经验去套一些比较刻板的概念 , 还是得去诚实地走向这些真实地人 , 这可能一个更好的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 。
李泞伶:竹子是一位前媒体人 , 现在在做一个线下的公益组织“Belonging space” 。 你对女性权益和精神健康这方面的偏向和你自身的亲身经历有关吗?
陈竹沁:我们的空间是两个女性联合创办的 , 可能是因为个人经历慢慢把关注点会放在性别议题上 , 我的合作伙伴以前是做精神健康艺术特展相关的公益组织的 , 我们就想尝试把在两个议题之间寻找一个交叉 。
无论是从身边的经验还是数据的统计上来看 , 女性抑郁的发生率更高 ,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社会结构的因素 , 而不只是个体精神的原因 。 所以我们在做这样一个线下空间的时候 , 一方面想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 让大家来讨论这些话题 , 同时也通过丰富的文化活动让大家能够找到一种归属感 , 就像它的名字所体现的那样 。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府城|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润富”之道
- 游客|百余项特色节会活动等你来!就地过年,青岛旅游送上“大餐”
- 文化|“我在新疆迎冬奥”达人西游第11季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启动
- 热经济|冰雪“热经济”将成万亿市场 这个冬天,你滑雪了吗?
- 确诊|本土新增65+5!张文宏:“这可能是最后一个‘寒冬’”
- 旅游|张家界景区启动“两亿礼包迎新春”旅游惠民活动
- 环球|年味满满!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开启首个“环球中国年”
- 荆州|荆州“放大招了”,2022年将有多个景点投用,助力城市知名度提升
- 安昌古镇|苏州“春节”值得一去的6个景区,来看看有没有你想去的
- 北青报|没故事的玲娜贝儿为何让人“上头又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