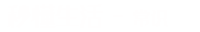在冬天的太阳底下打盹 , 也不会去跟书里的古人幽会 。 古人已经没有翅膀 , 无法捎带我们沉重的肉身 , 虽然我们在打盹的时候会感应到肉身的消失 。 打盹也就是打盹 , 小梦依旧是现时现实现世的 , 偶尔的不知身在何处 , 也远不及庄周梦蝶高妙 。 在冬天晒太阳 , 不管爬得再高 , 感觉到的依然是在季节的盆底——不可能还有低处 , 再低要么就是地狱 , 要么又是春天 。
秋雨整天整天地下 , 在我的感觉中它已经是世界性的了 。 想象整颗星球都因了秋雨湿漉漉的 , 而被濡湿的事物又都因了秋雨的张力而泛着幽光 , 心里总是腾起一种阅读神话的冲动;如果再把想象与太阳、北回归线、赤道、南回归线联系在一起 , 冲动里又多了知识的明澈;如果联系的是春分、夏至、秋分什么的 , 冲动里便添了农事的古朴与永恒 。
太阳的南移导致了秋天 , 那么是谁的离开导致了我的悲伤与思念?无论有无林徽因 , 我都感觉有时间从秋雨的张力里漫出 。 1987 , 1989 , 1991 。 它们 , 或者比它们更多的秋天秋雨 。 在这些年份里 , 确有与我亲密的人离去 。 泥泞是笔触 , 是秋天泼洒的颜料 。 我把脚放进去 , 在里面走 , 我就是梵高 。 尤其在黄昏 , 尤其在山区公路上 , 泥泞没有尽头 , 冷月的脸贴在两座山峰之间 , 河流在身旁的山谷奔泻 , 都有薄薄的乳白的雾缭绕 , 包括耳机里齐秦的歌声 。
在我的记忆与感觉里 , 齐秦的歌声一直都是属于秋雨和泥泞的 。 不只是山区公路的秋雨和泥泞 , 也包括小镇的秋雨和泥泞 , 也包括小镇的集市的秋雨和泥泞 。 我在小镇走动 , 出没在一朵朵惨白的塑料伞丛 , 像一只受伤的蚂蚁走在破烂的蘑菇群里(那一定是雨后的蘑菇 , 已为雨滴所伤) 。 雨水淋湿了头发、衣裳 , 泥泞裹住了脚 , 但我似乎要的正是这些 。 天空和人都失去了欲望 , 只剩下阴郁和空茫——安静的惨惨的阴郁和空茫 。 齐秦看起来是属于小镇上所有听力健全的人的 , 但事实上齐秦却仅仅属于我一个人 。 迷惘和不甘是齐秦声音的核质 , 也是秋天的我的生命的核质 。 当然更具感染力的是他歌声的忧伤——那真是秋天就要凋落的红叶一样的忧伤啊 , 真实得让我的触觉倍受威胁;亦似秋雨间歇的某一刹拉呈现的天光 , 潮湿多于干冽 , 凄美多于温暖 。 一个人本来在清冷寂寞的乡村校园 , 但因了齐秦的歌声 , 便到了潮湿泥泞的集市 。 齐秦的歌声对于我无异于绑架者手里的一根绳子 。
下细看 , 芭蕉已经呈现出衰败的迹象 , 颜色 , 轮廓 , 更主要是景象 。 白天看见的只是它的水淋 , 夜晚听见的才是雨打芭蕉 。 跟听雨打芭蕉相比 , 我还是更愿意听齐秦 。 雨打芭蕉是一种没有照应的空无的寂寞 , 而齐秦总是能让我思念一个具体的人 。 思念是可以炼就我们感情的特殊钢的 。 望一眼窗外湿透了的苦楝写几句 , 听两声雨打芭蕉再写几句 , 一封信便慢慢写成 , 从头到尾地读 , 边读边思念一个人 , 眼泪一点点流了出来 。 夜又黑又深 , 你没有办法不把那个人当着你唯一亮着的灯 。 想象自己飞跑在去邮电所的秋雨和泥泞里 , 冰冷的身子渐渐有了热气 。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家园|接力“晒” | 阿坝州三家园示范村之理县日波村
- 官鹅|“红”“绿”相映哈达铺,岷山脚下展新颜
- 超大|超大巨蟒现身阿里山?卷货车影片疯传网友惊呆
- 建设|接力“晒” | 阿坝州三家园示范村之金川县八步里村
- 官鹅|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老区新貌丨岷山脚下展新颜
- 阿尔山|自驾前往最合适不过的景点,不收一分钱门票,停车费只要十元
- 呼伦贝尔|这10座被遗忘的宝藏城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你认为哪座宜居?
- 阿尔山|去了汤加才知道,男女都不穿裤子;去了秘鲁才知道,胸大会被歧视;去了越南才知道,男人爱戴绿帽...
- 呼伦贝尔|内蒙古呼伦贝尔:杜鹃花开惹人醉
- 阿图柯|520邂逅硬派纯电SUV阿图柯 开启网红长沙的浪漫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