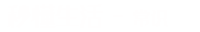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此刻,我在西安东郊的浐灞河边,遥望着京城的方向,不由想起北京冬天有关冰雪的记忆。

文章插图
资料图 王金辉 作图孩子小的时候,大都会问母亲,我从哪里来?很多母亲往往会说,你嘛,是从河沟里捡来的。如今,当我们步入中年,如果再问我从哪里来,其请教的对象便不是母亲,而回答的恰恰是你自己。这就如同儿时第一次看到雪花,我们在追逐中看到它一点点在手心中融化,你会发自内心地问:雪花为什么从天上来?为什么是六角形的?今天要寻找到答案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在网上一搜,一秒钟就知道答案。可是,对那样的标准答案我却本能地拒绝,因为那会限制我的想象力。
孩子的思维是富于幻想的,也是天然具有创造力的。上小学时,每到冬天,学生们就会在学校的角落里寻找废旧的桌椅。注意,我们可不是要学雷锋把废旧的桌椅修理成可以使用的,而是把那铁架子拆解下来,回家砸成单刀或双刀状,然后镶嵌在两块木板里,两边再系上四根粗线绳子。这样,一双简易的冰鞋就算完成了。除此以外,我们还自制了冰车、陀螺等冰上运动器材。至于溜冰场嘛,在郊区有的是鱼塘、河沟,那冰面虽然没有专业的溜冰场那么讲究,可也足以让我们这些农村娃玩个潇洒痛快。记得有一次在家门前的小河沟滑冰,那冰面尽管只有两米多宽二三十米长,可我依然能单脚双脚交替着滑,甚至还可以来几个旋转动作。滑过几次后,就不免有些得意,恨不得把小伙伴都叫来欣赏一番。有道是乐极生悲。一次,就在我完成了一个单脚旋转动作后,一个不小心,冰刀撞在一块裸露的砖头上,瞬间把我摔得四仰八叉,脑袋轰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待几分钟后醒来,我看了看蓝天,又摸了摸后脑勺,有个大包已经明显凸起了,好在没有出血。我慢慢起来,走到那块砖头前,用冰刀狠狠剁了一下便悻悻地回家了。
相对于冰天而言,雪地似乎更多了些许浪漫,但南方和北方的雪显然又是不同的。鲁迅先生在《雪》中这样描写:“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而在张贤亮的笔下,“黄土高原的雪绮丽无比。它比南方的雪要显得高贵、雍容、壮阔、恢宏大度;南方的雪使人感到冬天确实来临了,北方的雪却令人想到美丽的春天。雪,才是黄土高原上真正的迎春花。”其实,在我看来,不管哪种形态的雪,都是具体又抽象的,都是以人的心情决定的。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交通管制|峨眉山景区峨洪路出现冰雪道路 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
- 冰雪运动|“冬奥红利”显现 崇礼超3万人端上“雪饭碗”
- 文化|松原:做好冰雪旅游文章 加快推进“白雪换白银”
- 布局|Club Med长白山度假村正式开幕,加速布局中国冰雪假期市场
- 滑梯|大型烟花秀、激情大滑梯、网红冰雕!长春这个冰雪乐园免费入园!
- 七里坪|峨眉山景区峨洪路出现冰雪道路 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
- 崔宁|揭秘冰雪场:?滑雪场怎么“造雪”?5厘米厚的冰层要冻几天?
- 小萌新|宁夏泾源:六盘山下冰雪“热”
- 滑雪|相约冰雪,一起来丨首批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名单公布 巩固完成“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阶段性目标
- 冰雪|中国冰雪产业观察丨冰雪旅游乘“冬”风激活产业多元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