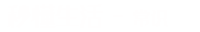当然,大徐也喜欢讲古文人的趣话,比如,他绘形绘色地讲述苏东坡和其妹互开玩笑的故事:苏小妹拿东坡脸长玩笑,撰联:“昨日一滴相思泪,今日方流到腮边。“苏轼则拿小妹的额高反唇相讥:”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小妹不服,又拿苏轼的络腮胡子说事:“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苏轼又拿小妹眼窝深反讥:“几回拭泪深难到,留得汪汪两道泉。”故事怕是后人附会,但能广泛流传,也体现了人们的一种情趣。
我们三人中,我虽然年龄小,但对文学有着特别的爱好和强烈的追求。除了订文学刊物,听文学播音,就是读文学书籍。上级下发的书籍中,有些文学方面的,比如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之类,我一般都从头到尾读。有时借书,比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杨沫的《青春之歌》等等。有时也买书,本地有的在本地买,本地没有的便借机到外地买。比如,有一次去北京出差,便顺手买了《鲁宾逊漂流记》、《宋词选》等书。工资不多,平时舍不得花钱,买书却毫不吝啬。别人的书读多了,也便心动手痒,自己试着写点。我甚至制定了一个写作计划:自十八岁开始,用十年的时间,力争成为一名作家。并且还有细化的分段,哪年在哪级刊物上发表短篇,哪年发中篇,哪年达到什么档次。只可惜,计划虽好,未能持之一恒,也就久久地徘徊,终无精进之功。
我对于诗词的爱好,应当说是最深的。这方面起步不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课本上很少有古人的诗词。我最早接触古诗词,还是在初中毕业时,看到某一墙上写有几首五绝,《静夜思》《登鹳雀楼》之类。读高中时,尽管我的课本上古诗文很少,但我却从父亲的书堆中找到几本文 革前的高中语文课本,在这里头,学习到屈原、宋玉等方面的内容。到了工作单位,又有读书时间,便更多地涉猎古诗文,尤其是古诗词。那时候读诗,真是如饥似渴,别说《唐诗三百首》之类,就是有些小说上的诗,也是不管理解不理解,拿过来就背。譬如读《青春之歌》,便将小说中提到的唐代李峤的《汾阴行》背了下来:“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再比如《红楼梦》里的诗词,我不能阅读全文,也找不清湘云、香菱的定位,但,诗是照诵不误。那个时期,刚刚粉碎四人帮,对传统文化的封锁刚刚有解冻的迹象,但《红楼梦》仍被一些人视为“淫艳”之书,不肯轻易出全本小说。我当时只能拿到一本《红楼梦诗词注释》,不太看注释,而是直接阅读和感受诗词。对《好了歌》这类,一个有志青年,哪里会理解它的看破红尘。但是这歌谣直白,一看就懂,所以很容易背得过去。至于长些的,古涩些的,也一样背。读“尺素鲛绡劳惠赠, 为君哪得不伤悲?”之类的句子,也曾感动了青春多情期的我。读“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也能带着不屑的眼光,看那些势利之人。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古镇|比苏杭古朴,这座江南小城,凭几座原味古镇让黄磊爱了多年!
- 建设|筑牢黄河绿色屏障——吕梁市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综述
- 松庐|惺惺有盘石,应记主人公 | 黄岩
- 班黄晨|看日出
- 天主教堂|黄山市有几个区几个县
- 孟门山|黄河之心,中华之魂!游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
- 濮阳|濮阳黄河边荒废的古村,摇身一变为网红打卡地,宁静而致远
- 黄龙洞景区|张家界景区送上80万份旅游礼包迎新春,总价值两亿元
- 江西|江西丰城小众古村,位于罗山之巅,民居皆是橙黄色外墙
- 黄龙|黄龙,如何成为人间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