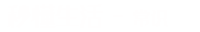文章插图
冬雪(油画)仲清华
【 鲍尔金娜|我想的雪神一定是个本土神,而且生活在东北的天上,但不是滕六 | 滕六】北京前天下了今年第一场雪。我在窗外空调上为野鸽子设置的野餐点被厚雪完全淹没。昨天上午鸽子们按时来吃饭,爪子落在松扑扑的白雪上,什么都抓不到,歪头看我,小眼珠转得有点谴责的意思。我就知道。它们飞走了,我等着雪快点融化,好证明我不是个随便断粮的坏人。我对北京的雪反正不是特别留恋,气温在这摆着,再漂亮的雪也留不住。
沈阳昨天下了今年第一场雪。家人告诉我,预告是暴雪,下到后来也确实有了点暴雪的意思。
父亲在小区迷宫一样的雪地里给想要下楼锻炼的奶奶踩出一条细细的小路,然后按照他“逢大雪则浴之”的习惯在雪地的白光下赤膊雪浴,平日不健身的人见了许是要觉得肉疼。我家的黑猫飞龙站在窗下望雪,耐心等我母亲放他去阳台玩。飞龙喜欢雪,站在雪地里也有水墨画的美,然而他对于雪是什么玩意始终想不通,每次出去踩雪,总要时不时回头紧张地盯我母亲,生怕她关窗。看起来是一条黑不隆咚的彪形大汉,内心却是个随时可能晕倒的贵族少女。
朋友说,她的孩子因为雪天停课了,停多少天不好说。我俩感叹,现在的小孩完全不知道扫雪的乐趣。当然,儿童不用在冷天室外做劳力,是社会的进步,我们那时候对于扫雪的异常狂热,多少也有点集体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特征。可是,现在的小孩不知道“雪停就是命令”这句话对于当年坐在中学教室里的我们有多强烈的吸引力,到底是错过了一点奇幻的经验。春游和运动会当然也令小孩子兴奋,可惜每年都只有一次,因果受制于人,期盼都变得机械化;可在东北冬天,雪神决定解放孩子们多少次,学校根本无能为力。哪怕考试卷子已经拍到桌子上,只要广播一句话,冬眠了一上午的后排同学也会以爽利的直角弹起来。一群人急着抢着出门取铁锹,零下二十度的空气里充满狂欢、不上进、疯疯癫癫的甜味,老师只能叹气。只要不上课,干什么都行,是我们那时候默认的精神理念。以扫雪的苦替换上课的苦,怎么看都合算——对我们来说,在雪里干活就是在雪里玩,守纪律也就是那么回事。怕冷怕感冒,是长大之后才学到的属性。
当然,一场扫雪如果真的只是扫雪的程度,那就完了。阳光一照,松软的雪地成了泥汤子,三两下就得收工回去继续上课,对我们来说是最欺骗感情的情景。一场真正让我们打高分的扫雪,灵魂全在于跟梆梆硬的冰坨子作斗争。除冰不是俏活,要出真力气,懂敲、砸、踹的技法,还得结合巧劲儿,更得靠人定胜天的决心。扫雪穿什么无所谓,戴再厚的帽子,睫毛也会冻得一根是一根,看世界全是亮闪闪的重影。挑选铁锹才是真正的讲究:最好用的是短粗杆的大脸铁锹,发力稳准狠,敲打雪壳子如有神助;那些行动缓慢的小孩最后都只能拿到杆子细长,锹面轻飘的破玩意,磕起冰来软若无骨,像小鸡叨米。有好铁锹的同学都不愿意跟有破铁锹的同学挨着,容易被老师认为干活不麻利,看起来也不专业。东北小孩子干什么都讲个有样儿,扫雪也不例外。除非有好铁锹和坏铁锹的同学彼此喜欢,那就没关系了。两个人默默窜到一起,帮彼此铲对方地界上的冰坨子,顺便唠点有的没的:“你冷不?”“不冷。”“晚上放学去桥洞底下吃炸鸡腿?”“我看你长得像炸鸡腿。”鼻涕都冻出来了也不丢人,毕竟是在那样寒冷而脆楞的蓝天下,四周都是咔咔敲冰的声音,说点什么都是秘密,气氛是很好的。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冬日|梅花:我想开了!这是衡东不可错过的冬日一景
- 浙江省|1、2月的梦想旅行清单出炉,我想去最后一个,你呢?
- 喀纳斯|1、2月的梦想旅行清单出炉,我想去最后一个,你呢?
- 良渚|良渚遗址公园里自然的“油画”,总会让我想到那个疯子艺术家梵高
- 杭州|等疫情过后,春暖花开,我想带你去看看这8个地方的美景,可好?
- 贵州|疫情过后,我想再去一次贵州,这10个地方,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 疫情|这个冬天,我想带你邂逅秦岭深处的醉美小城!
- 洲际赛|因为她,我想去趟马达加斯加
- 广元|中国最洋气的县城,壕出我想象
- 如果有一个下午用来放空,我想你可以选择西园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