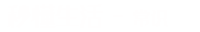槐花巷|寒露惊秋,各自消魂

文章插图
倘若灵魂生就一对翅膀——那么高楼也罢,茅舍也罢,又何必在乎管它什么成吉思汗,什么游牧群落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两个敌人两个密不可分的孪生子饥饿者的饥饿和饱食者的饱食
文章插图
By 茨维塔耶娃
寒露惊秋,各自消魂
同在一个城市,难得遇见槐花巷的邻人,而且那片曾经被槐花覆盖的洼地,已经矗立了高楼大厦,残存的三岔口,我从那里穿过一个美食街,耳目皆是陌生感,老宅所在的南岗车水马龙,盛夏我听过的蝉声,怕是在青石板下早已不知多少轮回,这又迥异于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的眷恋,槐花巷太微小,夜深人静,巷头巷尾,什么动静都被过滤为一只灰猫的警惕。乡愁基本皆是伪乡愁,况且槐花巷距离太近,仅仅因为太近,让我找不到就令人抓狂,类似帕慕克的叹息,“我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没离开过童年时代的房屋、街道和邻里……”,实际上,其间帕慕克还是短暂离开过伊斯坦布尔,随后的归来,我试图和他一样,既是深陷其中遵循内心的自我,又是时而清醒时而模糊的旁观者,除了耗在淮北和平顶山连贯的数年,另外什么时间,我一直呆在这个不南不北的小城,目视着槐花巷的槐花和青石板在渣土车的碾压时缓缓消弭。
文章插图
在2018年洛夫去世前几年,温哥华的友人给我捎来一本洛夫签名的诗集,那是怎样意外中的惊喜,有时候浮现出弘一法师枯槁沉郁的“悲欣交集”,坚持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好在友人与洛夫为邻,诗人也是近乡情怯,他把故乡衡阳看成“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至于我那颇有经历的友人,他的乡愁,疫情之前,即是两年回归小城,天天醉于故人的回忆之中。毫无例外的结果,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村上依旧热门陪跑,米兰·昆德拉寂寞呆在热榜的末尾,赢家是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我对他很不熟悉,连这个名字都是临时起意复制粘贴,但这并不影响评委们日趋偏执变态的趣味,如果趣味也叫趣味的话,不过古尔纳又是一位移居英伦的作家,不难想到,在此之前同样因为差不多背景获奖的石黑一雄和奈保尔,其中蕴含了共情的乡愁,是否伪乡愁不得而知,或许文学该到了撕裂自己也撕裂评委不知如何表达的境地。
文章插图
他们之中谁获得诺奖非吾辈所能妄言,不过是个奖项而已,小说家描述着欲望种种,也包括了诺奖,毕竟有包含着金钱的诱惑。盛夏正酣,女同学中最有亲和力号召力的W同学,留言要把一套刚买不久石黑一雄的小说送给我,不免有些感动,这些年人际往来,鲜有人送我书籍了,遂快马加鞭搜集材料搭配了一只手串,与石黑一雄放在一起表达投桃报李也算差不多的趣味。大抵在诺奖之前,石黑一雄也是个颇为神秘和遥远的存在,仿佛我寻找槐花巷未果,空荡荡的情绪一直漂浮在城市上空,最早看过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确实是在诺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很不开心,与小说和文字交流是唯一减负的去处,小说中男管家一直寻找的尊严,都被写作者克制压抑地藏在古板冗繁的长句子里,此起彼伏,不紧不慢,在此过程中,真值得追寻真相,还原自我吗?生活的重压之下,个性不名一文,或许,不是我们选择,而是选择挑上了我们,无所谓改变什么,生存才是硬道理。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金色|小时候的味道
- 诗与远方|寒露为“寻找成渝文旅新地标”打call:这种精神的地标应向全世界发布
- 白蜡|秋天的白蜡树
- 茶园|带着深秋的甘醇,茶汤里飘扬着清冷,深秋白茶寒露茶踏着暗香来了
- 寒露已过,邂逅密云醉美深秋|水光潋滟?红叶诗韵| 红叶
- 红叶|寒露已过,邂逅密云醉美深秋
- 秋光|明日重阳!黄花红叶、妆点秋光...
- 寒意|扬州:寒露方至 家园已秋
- 寒露|已是寒露,赏颐和园的秋
- 艺尚|寒露至 临平千亩向日葵花海迎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