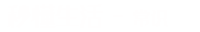舒飞廉|【风土记】乡村可畏 | 江老师

文章插图
我刚回乡下那几年,胆子还不算小。再远再陌生的村子,也是敢去的,村口枫杨树白杨树下,土狗们探头探脑,巷子里还有可疑的大白鹅在立颈张望,蹑手蹑脚走过去就是了。能天不亮就出门,朝着小澴河鱼肚白的黎明,深一脚浅一脚地慢跑,遇到河边穿连帽长雨衣,眼神冷厉,手持电鱼杆的捕鱼人,也是心如止水。晚上在灯下看书累了,推门出村,沿着村西的大路向破败的学校走,天上明星繁繁,北斗七星铁钩一样,悬置在舒家塆的村树上,摆脱掉象征界符号界的纠缠,走在蛙声、稻香、星光与夜露里,我的身体是放松的,心情是愉快的。
最近我不太敢清晨出门跑步了。往晏家塆的土路不走,由肖家河绕上小澴河堤也不行,并不是像《诗经·召南》里那位清早出门的女人,“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担心打湿鞋,牵惹是非,而是有一点怕蛇。虽然只遇到过一两次,也没有弄明白是水蛇还是“火桑根”(赤练蛇),蛇可能更怕人,远远地滑进青蒿丛里,我就有一点像惊弓之鸟,忧心于杯弓蛇影了。总不能穿着雨鞋跑步吧?那些路边的竹林也非常的可疑。我所盼望的乡村的神荒,一点一点地临近了,不仅是野猪野象、鼋鼉鱼鳖会重归故里,野狼呢?吊睛白额大虎呢?蛇呢?小澴河会欢迎它们,河边的人也会欢迎?之前我看见小飞蓬与狗尾草离离在路边,觉得还蛮诗意的,这几年看见苍耳一片片席卷着堤坝,深秋里黑铁般支棱着枝柯,掷出它们带钩的小地雷,《诗经》里,采采卷耳有诗味,要是改成“采采苍耳”,会让我们读者手忙脚抖,心烦意乱吧。向南经汪寺村上小河堤,路边是白杨树,我散步常去,曾写过《枫杨好看,白杨好听》文,一群群喜鹊常绕着杨树奋飞。去年冬天,霜雪未销,草黄树黑,我跑上堤坡的时候,第一次在本地发现了乌鸦,百千计的乌鸦站在电线上、枯枝上,“彼其之子,硕大无朋”,又一个个圆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掏出手机的我,好像是“与子同仇”的车马阵,杀气腾腾。我赶忙转过身继续向前跑,那一刻,后背是隐隐发凉的。
文章插图
我被狗狗们从小追到大,最近也有点变本加厉。从前我们这边,还是非常纯正的中华田园犬,下雪天,也是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黑狗都很少,因为有人说黑狗最好吃。和当下流行的柴犬比较起来,它们也很少笑呵呵的样子。它们的“狗生观”简单得很:对家人俯首帖耳,无限忠诚,对陌生人是狂吠如豹,龇牙咧嘴,在“我们”与“他者”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只要不越过这条界线,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万一被它们狂追,逃出这条界线,就是生天。可是这些我用无数克的肾上腺素换来的经验,现在已经变得很可疑了。附近村里的人,像接受二手衣服、二手汽车一样,接受城里的“二手狗”。这些来历不明的狗又与本地狗交往,其乐融融,重新乡土化,用它们的尿液努力划分各自的领地,令从前的躲狗地图多半失效。当你对一只陌生狗狗的攻击力与攻击范围失去判断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绕道,君子不立于恶犬之前。狗犹如此,牛又何尝不是这样。大小澴河堤上草长鹭飞,日下已开辟成养牛的草场,传统的水牛与黄牛之外,也会有黑白相间的奶牛与其他花色不同的牛,这些牛的主要职责,已经不是去担当耕作的重任,成长为劳动的模范,而是默默吃草长肉,默默走进寒光闪闪的肉联厂。它们没有经过老农的规训,一身蛮力未发泄在田园中,又面临着悲惨的未来。我每次在窄窄的堤道上与它们擦身而过时,心里也是慌乱的。来养牛的、种铺花园用的结缕草的,种小香葱的,放蜜蜂的,放鸭的,也不是本地人,而是游动的,说着不同方言的外乡客。我认得的面熟的老一辈邻村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暂停|雍和宫自2022年1月17日起暂停开放
- 乡村|大论坛赋能小渔村
- 景区|居庸关长城景区封闭
- 冰雪运动|梦幻冰雪之城:内蒙古兴安盟
- 运河|江苏淮安:拥抱运河 再续华章
- 暂停|居庸关长城景区1月19日起暂停对公众开放
- 文化|【站在新起点】打造不夜地标 激发消费动能
- 居民|发改委:乘势而上扩大居民冰雪消费
- 假古镇|山东又一座“假古镇”走红,投资6000万建成,门票仅需40元
- 宏宇|勃利县冬捕节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