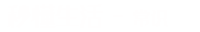冯敏昌|孟州地名说:古周城村,一座建于2600年前东周时期的城池( 三 )
整个历史事件,实际上就是晋文公为“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自导自演的闹剧。因此,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在讲究“正统”“礼制”的儒家史书中对此事的记载耐人寻味了。《竹书纪年》“天王会诸侯于河阳”。《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正如《史记》中所说“书讳曰”。
为什么史书会有“书讳曰”这三个字呢?因为,一个诸侯以命令的口吻,把一个国王召到王宫之外的诸侯国晋地来接见大臣,这是一件多么不光彩的丑事,对一个国君来说,是一种耻辱,也是对封建君臣之礼的最大践踏,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孔子在整理《春秋》时,对此事既感到愤怒又感到悲哀,为了维护周王的尊严,孔子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训”,就是规矩、制度、礼义,孔子的意思是:这件事是不合“礼法”的。孔子把此事记述为:“天王狩于河阳”,狩字并非仅有“狩猎”之意,还有“巡察”之意,一个“狩”字,既记载了历史事件本身,又有 “尊王”之意,维护了周王仅有的一点尊严。
三
文章插图
《左传》记载“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乡役之三月。”魏晋时期杜预作注时说:“衡雍,郑地,今荥泽卷县。襄王闻晋战胜,自往劳之,故为作王宫……”杜预认为践土城位于今天的新乡市原阳县西北。
冯敏昌先生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编写《孟县志》(冯志)时,对康熙《孟县志》(乔志)中提出的“周襄王宫,《左传》晋文公胜楚而归,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乡役之三月。衡雍即今洪(横)涧村,王宫在北原上”观点提出了质疑:“古城在五龙口东南八里许北原上,三面临润,后倚龙原,长岭四抱,东南微见嵩邙,风气回聚,颇具形胜,惜居民寥落。城南址高尚丈余,长一里许,中断如门,遥望可见。旧志(指康熙《孟县志》)所谓王宫城者是也。然于地望不协、又介驷百乘,徒兵千即献,虑不能容矣。前已辨说,兹难别考,缺乏而已。”
冯先生虽然承认古城是古代一座重要的军事城池设施,但却因此城面积太过狭小,容纳不下“百驷千兵”,使“觐见”之礼的相关活动在城中根本无法展开为理由,否定了古城是践土城的结论。
冯先生的结论有点武断了。一般来说,古代的城池规模都不大,当时的王宫城是晋文公派兵“乡役之三月”而成,规模一定不会很大,但作为举行献俘仪式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况且,“献俘仪式”并不是此次盟会的重要程序,再说,献俘并非一定要在城内举行,在城南旷地上也是完全可以举行。
不论是军事家的杜预还是金石学家的冯敏昌,他们的注疏和怀疑都忽略了选择会盟地点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晋文公之所以要召集各诸侯国到践土城进行会盟,主要的目的是晋文公为了称霸各诸侯国,让各诸侯国承认他为各诸侯国的领导。但是,如果他自封为王,则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他还需要借助周王室这个早已成为傀儡的“正统”者的威望,只有这样他才能站在道德的高地,把自己打扮成“正统”的代言人,在名义上势压群雄。因此,他把诸侯召集在一起会盟,这个会盟地点必定要选择在晋国势力内的一个最适当地点,以此来抬高晋国在各诸侯国的影响力。为达到这一目的,晋文公决不会把这个会盟地点选在晋国势力范围之外的郑国某地,或者其它诸侯国的某地,而使其它诸侯国一时成为天下人的关注重点。所以乔腾凤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衡雍即今横涧村,践土即古周城村。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 内蒙古自治区|全国第二批5C、4C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名单出炉
- 武威|这个省的地名也太太太霸气了吧!
- 镇江|江苏最“难读”的4个地名,都是最佳旅行去处,你认识这些吗?
- 度假|首批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名单来啦 北京延庆海陀入选
- 公示|首批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名单来啦 北京延庆海陀入选
- 张家界|张家界冷门景区,位于市区重新开放,由多地名匠修建,沉稳大气
- 文化遗产|第九批安徽省千年古镇、千年古村落地名文化遗产候选名单公示
- 自驾|第二批5C、4C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名单公示
- 百丈漈|15红枫古道
- 名单|2021年四川省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名单公示!四姑娘山等6地进入公示名单